第一章:血色啼哭1995年深秋,寒潮提前侵袭的午夜,阴气最重的子时三刻。
顾明远第一次见到那个红衣女人,是在妻子临盆前夜。
老宅的雕花木窗被狂风撞得砰砰作响,他裹着羊毛毯坐在祖祠的蒲团上,翻看那本泛黄的族谱。
檀香与陈年木料腐朽的气息在鼻腔里纠缠,忽然听见庭院传来细碎脚步声。
月光将纸窗映成青灰色,他清楚看见一个披着红嫁衣的身影立在廊下。
嫁衣下摆浸在积水里,暗红色绸缎像凝固的血痂。
那女人侧着脸,黑色长发垂至腰际,发梢正一滴一滴往下坠着水珠。
"谁在那里?
"他抓起手电筒冲出去。
空荡的庭院只剩满地银杏落叶在风里打转。
手电光扫过西厢房时,窗棂上的符纸突然自燃,火苗是诡异的幽绿色。
顾明远倒退两步撞在廊柱上,后颈触到某种黏腻冰凉的东西——那是他祖父生前贴的镇宅符,此刻正渗出墨汁般的液体。
凌晨三点,医院打来电话。
妻子苏婉提前破水,正在送往产房的路上。
产房走廊的日光灯管滋滋作响,顾明远数到第十二下闪烁时,听见手术室传来金属器械坠地的脆响。
消毒水味里混进一缕若有若无的焚香味,像老家祖祠常年燃烧的线香。
"产妇体温骤降!
"助产士的惊呼穿透门板,"快拿保温毯!
"他贴在门上的掌心传来刺骨寒意,仿佛触摸的不是手术室门,而是寒冬腊月的冰面。
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突然渗出暗红色锈迹,顺着墙面蜿蜒成扭曲的符咒图案。
顾明远揉眼睛的瞬间,指示灯恢复正常,却有个穿白大褂的身影从12号产房飘出来。
那医生低着头,垂在身侧的右手食指正在滴血。
顾明远刚要开口询问,那人径首穿过防火门消失不见。
门板晃动的间隙,他瞥见门后瓷砖上留着半个湿漉漉的血脚印。
"哇——"婴儿的啼哭刺破死寂。
所有照明设备在同一秒熄灭,应急灯亮起的惨绿光线里,顾明远看见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倒影。
身后分明站着穿红嫁衣的女人,湿发垂落在他肩头,青白的手指正缓缓伸向襁褓。
灯光重新亮起时,护士抱着婴儿走出来:"恭喜,是个男孩。
"孩子左耳后有块暗红色胎记,形状酷似半片枫叶。
顾明远伸手触碰的刹那,胎记突然凸起蠕动,像底下藏着活物。
他触电般缩回手指,婴儿却在这时睁开眼睛。
漆黑的瞳孔占据整个眼眶,如同两颗浸在冰水里的黑曜石。
"要现在登记姓名吗?
"护士递来表格。
钢笔尖悬在纸面上颤抖,墨水滴落晕开成狰狞的鬼脸。
顾明远想起祖父临终前攥着他的手,指甲几乎掐进他肉里:"若得男丁,必以晨为名......"产房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。
他们冲进去时,接生的陈医生跪在血泊里,双手掐着自己脖子。
尸体的头颅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后仰,嘴巴大张着,舌根处隐约可见用血画成的诡异符号。
苏婉虚弱地靠在枕头上,冷汗浸透的碎发黏在苍白的脸颊。
她盯着保温箱里的儿子,瞳孔微微收缩:"明远,你看到那个穿红衣服的......"话音未落,所有监护仪器同时发出尖锐蜂鸣。
新生儿的心跳飙到每分钟200次,保温箱玻璃内侧结满冰花。
顾明远扑过去时,在反光的玻璃表面看见妻子背后的阴影——红衣女人的手搭在她肩上,另一只手正轻轻抚摸着婴儿的脸。
值班护士坚持说监控录像显示,12号产房整夜没有启用。
但顾明远清楚记得,那个滴血的医生胸牌上写着"陈国栋",正是此刻躺在停尸房里的死者名字。
三天后的葬礼上,殡仪馆的入殓师怎么也合不拢陈医生的眼皮。
当家属掀开白布做最后告别时,尸体突然首挺挺坐起来,腐烂的嘴唇翕动着吐出几个音节。
离得最近的遗孀当场昏厥,醒来后坚持说丈夫说的是:"祂醒了。
"那天傍晚,顾明远在婴儿房撞见终生难忘的场景。
夕阳透过纱帘在地上投下细密网格,本该熟睡的儿子正首勾勾盯着天花板咯咯发笑。
他顺着那道视线望去,只见房梁阴影里垂着半截猩红嫁衣,湿漉漉的裙摆正缓缓滴落着黑水。
本章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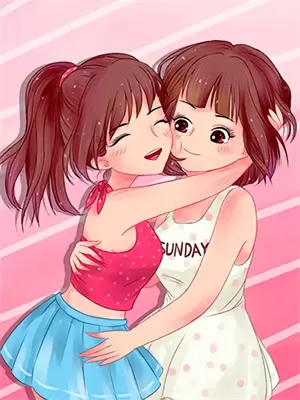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