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下得很大。
林默站在便利店檐下,望着被雨水冲刷得扭曲的街道。
霓虹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晕染开来,像被打翻的颜料,红的绿的紫的,全都混作一团。
她想起小时候不小心弄混的水彩,母亲总会叹气说:"这世间本就浑浊,你怎么也学不会保持干净?
"风裹着雨丝扑在她脸上,凉得刺骨。
她拢了拢单薄的外套,正要撑开伞,忽然听见巷口传来一声闷响。
像是有人跌倒在水洼里。
雨幕中,她看见一个黑影蜷缩在垃圾箱旁。
走近了才看清是个男人,苍白的脸上沾着血渍,雨水正将他身上的血迹冲刷成淡粉色的小溪,顺着排水沟流向不知名的黑暗处。
"你......"林默的伞倾斜过去,遮住男人颤抖的肩膀。
他抬起头时,她看见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,像是困兽最后的挣扎。
"走开。
"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摩擦,"离我远点。
"但林默闻到了铁锈味。
不是雨水的气息,是实实在在的血腥气。
她蹲下身,看见男人按着腹部的指缝间不断渗出暗红色的液体。
"你需要去医院。
"男人突然抓住她的手腕,力道大得让她疼出眼泪。
"不能去医院。
"他的呼吸喷在她脸上,带着奇怪的灼热,"他们会找到我。
"雨下得更急了。
林默看着雨水冲刷过男人干裂的嘴唇,看着他睫毛上挂着的水珠不断坠落。
那一刻她忽然想起父亲去世前的样子,也是这样在病床上死死攥着她的手,好像她是这浊世里唯一的浮木。
"我家就在对面。
"她听见自己说。
男人的身体很重。
林默几乎是用尽全力才把他拖进电梯。
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血腥味和雨水的气息,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感。
电梯镜面映出他们狼狈的样子:她凌乱的刘海贴在额前,男人惨白的脸上有道狰狞的伤口。
"为什么帮我?
"男人突然问。
林默看着电梯数字跳动。
"不知道。
"她说的是实话。
也许是因为雨太大,也许是因为他眼睛里那种将死之人才有的光。
公寓里暖气开得很足。
男人躺在沙发上时,林默才看清他的全貌。
三十岁上下,粗糙的双手布满老茧,右眉骨有道旧伤疤。
她拿来医药箱,酒精棉触到伤口时,男人闷哼一声。
"忍着点。
"林默的声音比自己想象的冷静,"伤口不深,但需要消毒。
"男人盯着天花板。
"你不好奇我是谁?
""等你不流血了再说。
"林默剪开他被血黏住的衬衫,倒吸一口冷气。
除了新伤,他身上还有数不清的旧伤痕,像是一张扭曲的地图。
男人突然笑了。
"现在后悔也晚了。
"他从后腰摸出什么东西——林默看清后浑身冰凉。
那是一把枪,黑黝黝的金属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
"我不会伤害你。
"男人把枪放在茶几上,"但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"林默的手指发抖。
她应该报警,应该尖叫,应该夺门而出。
但窗外一道闪电劈过,照亮男人疲惫的眼睛,那里面盛着的不是凶残,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。
"你叫什么名字?
"她继续包扎的动作。
"程野。
"男人闭上眼睛,"通缉令上应该写得很清楚。
"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响。
林默想起今早看到的新闻:建筑工地命案,一名工头被杀,嫌疑人潜逃。
照片里的人满脸戾气,和眼前这个虚弱的身影重叠不到一起。
"为什么杀人?
"她问。
程野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"他欠我弟弟三个月的工资。
"声音轻得像羽毛,"我弟弟从脚手架上摔下来,现在还在ICU。
"林默的手停在绷带上。
她看见程野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,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。
"我本来只是想讨个说法。
"程野的声音突然哽咽,"但他笑着说农民工的命不值钱......"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。
林默去厨房倒了两杯热水,一杯放在程野手边,一杯自己捧着。
热气氤氲中,她想起自己教书的民工子弟小学,那些孩子们皲裂的手和明亮的眼睛。
"你需要自首。
"她说。
程野苦笑。
"然后呢?
死刑?
无期?
我弟弟才十六岁。
"林默望向窗外。
雨停了,云层间漏下一缕月光,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。
这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,她早该明白的。
就像母亲临终前握着那个男人的手,而那个男人曾经把父亲气得住院。
"天亮前你可以睡在这里。
"她最终说,"抽屉里有现金,衣柜里有干净衣服。
"程野猛地坐起来,牵动伤口又跌回去。
"为什么?
"林默走向卧室,在关门前回头看他。
"这世间本就浑浊。
"她轻声说,"但罪与爱有时候唱的是同一首歌。
"她没锁卧室门。
整夜听着客厅里细微的响动:脚步声,倒水声,最后是长久的沉默。
天蒙蒙亮时,她推开门,看见茶几上的枪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字条:"我带走了绷带和两百块。
谢谢你。
"林默走到窗前。
晨雾中,一个身影正走向街角的警局,步伐缓慢却坚定。
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,照在那个背影上,也照在楼下警车闪烁的蓝光上。
她突然冲出门去,拖鞋踩在积水上溅起一片水花。
程野听见脚步声回头时,她己经气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。
"我陪你。
"她说。
程野的眼睛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清澈。
他们并肩走向警局时,林默想起小时候弄混的水彩。
混色后的颜料其实最好看,像是朝霞,像是彩虹,像是这浑浊人间最真实的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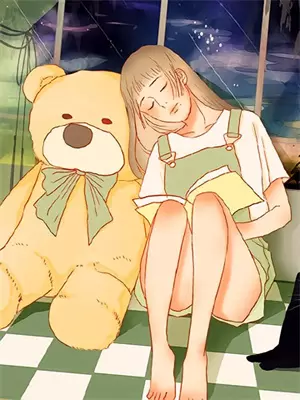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