雅加达港的汽笛声还在耳蜗里轰鸣,我已经站在了故乡湿润的晨雾中。
行李箱滚轮碾过青石板路的声响惊飞了檐下的家燕,翅膀掠过褪色的春联,露出“早生贵子”四个金漆剥落的字。
门环上的铜狮子含着锈绿的环,叩击声在巷弄里荡出三年前的回音。
门轴吱呀着旋开时,带出一团裹着茉莉头油味的雾气。
玉兰系着那条蓝底白花的旧围裙,围裙下摆沾着结成硬壳的米糊,左手还攥着半截没剥完的毛豆。
她身后探出个小脑袋,头发剃得能看到青白头皮,眼睛像黑葡萄似的发亮,却在与我视线相触时嗖地缩回门后。
“小雨怕生。”
玉兰用围裙角擦我肩头的露水,这个动作让记忆突然闪回——三年前安检口分别时,她也这样擦拭我西装上不存在的皱褶。
如今她指节粗了许多,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姜黄,那是常年腌制酱菜留下的印记。
阁楼的老式座钟敲响十下,铜摆晃动的阴影投在积灰的楼梯转角。
我弯腰去提行李箱,后颈忽然掠过一丝凉意。
回头正撞见那孩子躲在博古架后偷窥,他迅速把拇指塞进嘴里吮吸,这个动作让我的心尖莫名发颤——孕期手册上说,胎儿在母体里就会吮吸手指。
“给小雨的。”
我摸出印尼带回来的椰壳玩偶,铁皮发条硌得掌心发疼。
孩子赤脚踩着砖地挪过来,脚趾甲缝里还沾着新鲜泥巴。
当他伸手触碰玩偶时,我看见他耳后那颗朱砂痣,像极了玉兰娘家祖传玉佩上的沁色。
玉兰突然打翻了搪瓷盆。
滚落的毛豆在砖地上蹦跳,有几颗钻进八仙桌底。
她蹲下身捡拾时,后颈脊椎骨凸起得厉害,仿佛随时要刺破那层苍白的皮肤。
怀孕时她总抱怨腰疼,视频里她扶着后腰说孩子在踢她,我却只听见雅加达港永不停歇的海浪。
黄昏时下起细雨,老宅的瓦当开始滴水。
我站在二楼回廊晾衬衫,瞥见玉兰抱着小雨在天井转圈。
她哼的还是那首《月光光》,但尾音带着喘不上气的颤抖。
孩子手腕上的银铃随动作叮咚作响,我忽然想起出国前夜,她把红绳系在我行李箱拉杆上,说铃铛能驱赶异乡的恶灵。
深夜被哭声惊醒时,月光正斜照在五斗橱的雕花上。
循着声源摸到西厢房,玉兰披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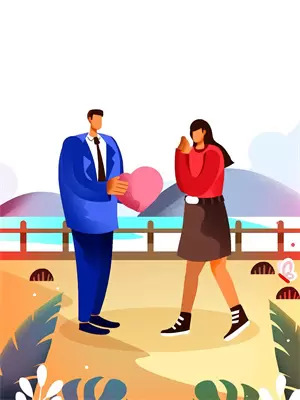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